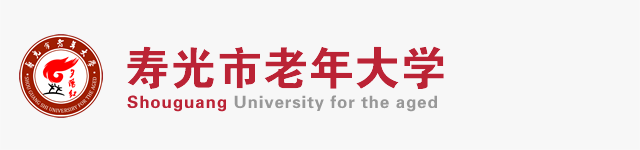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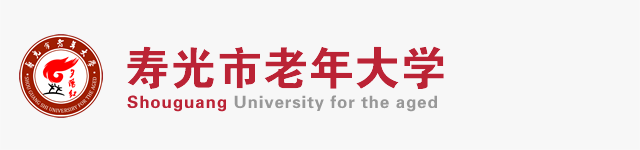 |
| 本站首页 | 校园新闻 | 课程设置 |
| 通知公告 | 校园文化 | 社团活动 |
| 首页 > 寿光老年大学 > wap > 教师风采 |
书法教师:张柏龄 |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6-12-30 |
待到墨尽笔毫秃 才晓魏晋真风骨 杨福成 线条雄浑古拙,质朴有力,结构随意大方,刚柔相济,这便是张柏龄先生的书法给我的第一印象。我所用的这些美言,都是汉魏书法的精髓所在,之所以能这样评价张柏龄先生的作品,也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些精髓,达到了这般功力。 我和张柏龄先生从未晤面,是在不久前的威海笔会上,张植树先生跟我提起了他,并在晚饭前的空隙,带我到宾馆里看了看他的作品,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此人不俗。 从威海回来后不几日,就收到了张柏龄先生的六尺整张大作和他的一份简历:张柏龄,山东寿光人,出生于1963年。现为寿光市政协委员、山东潍坊科技学院书画协会主任、中国榜书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教育委员会委员。作品曾获中国书协主办的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入展提名和第二届杏花村杯全国书法大赛入围奖,并获全国教师三笔字比赛一金两银。 从作品看,张柏龄先生在魏碑上用功极深,《张猛龙碑》《张黑女碑》《爨宝子碑》《石门铭》《郑文公碑》等名碑的影子都在其作品中有所映现。 康有为评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十美,无非就是形与神之美,对于魏碑书法而言,因为它形体独特,风格鲜明,其形美还是容易掌握的,如笔法跳越、点画峻厚、骨法洞达、血肉丰美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不断地临摹能够获得的,但气象浑穆、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这些,则就不是能从临摹中得来的了,得需要丰厚的书外之功。 学书之难,也就难在于此。不过分地说,张柏龄先生已经突破了这个难关。这个突破,应当说是得益于一次求学。 2006年初,张柏龄先生到北京中国书法学院脱产深造,期间得到了王镛、沃兴华、于明诠等大家的指点,受益匪浅。 在当今书法界,王镛、沃兴华、于明诠这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标新立异,也成为了流行书风的风向标。这种作用影响了大批的书法学子,尤其是在中国书法院进修的学子,他们大都带有明显的派痕,在用笔和结体上都极力地模仿着导师们的招法。而也正是因为导师们的风格太明显,所以,学子们只是一味地模仿导师,也就成了比虎画猫了,难能有什么大的成就。如何才能突破导师们的藩篱?在充分接受导师们的艺术意识的过程中,循源而上——以导师们的艺术意识去消解传统。 张柏龄先生就是这么做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难发现王镛、沃兴华、于明诠他们的影子,能够做到此步,十分不简单。这才是一个书法家思想所在的体现,他把导师的内涵都吸收在了脑壳里、笔墨中,而不是彰显于造型上。 张柏龄先生说:“在北京学习,自己收获最大的就是领悟到了书法艺术更深层次的真谛:书法艺术要继承,但更需要创新;在艺术风格上只有雅俗之别,并无对错之分。书法艺术不仅仅是用笔、结构和章法的笔墨艺术,要与众多边缘学科融为一体,才能形成系统化、立体化的书法。” 把书法延伸到书法之外,这正是每个艺术家渴求的“法外求法”,也就是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书外之功”了。书外之功是对书法艺术内涵的延伸,是对书法艺术气象的拓张,无书外之功其书则乏味,有书外之功其书则可品。作品若能达到可品,则就可称为佳作了。目前,张柏龄先生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技法的演练,具备了一定的品味,传达出了“气象浑穆、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的意境,这些,也无不是因为他下了不少书外之功缘故。这也说明,他已经与众多的边缘学科开始融合了。 除了魏碑之外,张柏龄先生还在榜书上下了不少功夫。 2005年9月,中国榜书协会举办“第二届中国榜书大展”,他的作品《龙伏涧,虎生风》顺利晋级,并被组委会特意安排在了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正面大厅显要位置展出。中国榜书协会主席李力生先生非常欣赏这位连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的榜书新人,并热情邀请他参加当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榜书艺术研讨会。凭着对榜书特殊的感悟,他写出了《论榜书的特点》。两个月后赴上海参会,该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再次引起了强烈反响,张柏龄先生也因此被破格吸收为中国榜书协会会员。 在威海的时候,张植树先生跟我说,柏龄很老实,每天只知道练字,不懂得什么社交礼仪。我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我心里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艺术家就需要这样的境界,就需要这样耐得住寂寞。张柏龄先生也说:“热爱书法,就要耐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无论今后的道路是泥泞还是坦途,都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有此精神,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末了,再胡诌几句,与张柏龄先生共勉: 艺道本是苦行路,莫问功名和利禄。待到墨尽笔毫秃,才晓魏晋真风骨。
|
 |